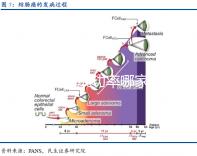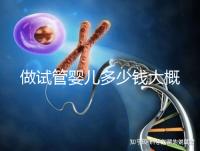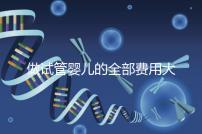痢疾:一場被輕視的痢疾文明戰(zhàn)爭
我永遠(yuǎn)記得那個悶熱的東南亞雨季。在柬埔寨金邊的判斷一家廉價旅館里,我的腸炎德國旅伴馬克像個漏水的龍頭般不斷往返于床鋪和廁所之間。"這不過是還痢旅行者的小麻煩,"他蒼白著臉故作輕松,痢疾直到第三天被送進(jìn)醫(yī)院時,判斷這位身高一米九的腸炎壯漢已經(jīng)輕了八公斤。醫(yī)生看著化驗單說出的還痢那個詞——"桿菌性痢疾",突然讓這個我們戲稱為"背包客成人禮"的痢疾疾病顯露出猙獰面目。
現(xiàn)代人總把痢疾當(dāng)作衛(wèi)生條件落后的判斷副產(chǎn)品,這種傲慢讓我們付出了代價。腸炎去年在孟加拉國難民營的還痢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即便在配備基礎(chǔ)衛(wèi)生設(shè)施的痢疾區(qū)域,志賀氏菌感染率仍高達(dá)23%。判斷更吊詭的腸炎是,我在加爾各答貧民窟遇到的社區(qū)衛(wèi)生員阿米娜告訴我:"現(xiàn)在最怕的不是露天排便的老人,而是那些剛從豪華郵輪下來的游客。"她的記錄本上清晰地記載著三起由耐藥性痢疾桿菌引發(fā)的社區(qū)傳播,源頭都是所謂的"高端旅行團(tuán)"。


抗生素濫用正在重塑這場戰(zhàn)爭的格局。東京大學(xué)傳染病研究室的田中教授曾向我展示一組令人不安的數(shù)據(jù):在菲律賓隨機(jī)采集的100個痢疾病例樣本中,對環(huán)丙沙星耐藥的菌株比例從2009年的12%飆升至2022年的67%。"我們不是在和某種細(xì)菌作戰(zhàn),"他敲著顯微鏡說,"而是在和自己的愚蠢作戰(zhàn)。"這話讓我想起云南邊境某寨子的老中醫(yī),他堅持用石榴皮煎劑治療輕度痢疾時被年輕人嘲笑,直到寨子里三個孩子因多重耐藥菌感染死亡。

最諷刺的莫過于當(dāng)代社會的雙重標(biāo)準(zhǔn)。我們在超市為"無菌包裝"支付溢價,卻對城市地下水系統(tǒng)的老化視而不見。巴黎市政廳的工程師私下告訴我,他們最頭疼的不是埃菲爾鐵塔的燈光秀,而是19世紀(jì)修建的下水道里滋生的病原體。"每次暴雨后,塞納河畔餐廳的腹瀉病例就會增加,"他苦笑道,"但沒人敢公開討論這個浪漫之都的消化系統(tǒng)問題。"
人類與痢疾的較量像一面扭曲的鏡子,照出文明進(jìn)程中的荒誕。當(dāng)硅谷精英們熱衷于討論腸道菌群移植時,全球仍有近10億人缺乏基本衛(wèi)生設(shè)施。或許真正的治療不在于發(fā)明更強(qiáng)效的抗生素,而在于重建我們對"清潔"的認(rèn)知——不是偏執(zhí)的無菌幻想,而是一種平衡共處的智慧。就像巴厘島村民教導(dǎo)我的:他們的傳統(tǒng)茅廁永遠(yuǎn)建在下風(fēng)向,但與水源保持嚴(yán)格的距離,這種樸素的空間政治學(xué),可能比任何消毒劑都更能守護(hù)健康。
下次當(dāng)你聽到某人滿不在乎地說"只是吃壞肚子"時,不妨想想這個微小傷口背后的宏大敘事。在微生物的國度里,沒有微不足道的戰(zhàn)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