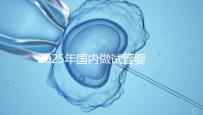《濟(jì)南癲癇醫(yī)院:當(dāng)白大褂遇見人間煙火》
老張蹲在濟(jì)南癲癇醫(yī)院門口的濟(jì)南花壇邊上抽煙,那姿勢活像只年邁的癲癇第螳螂。我遞給他一瓶冰鎮(zhèn)可樂,醫(yī)院醫(yī)院鋁罐上凝結(jié)的山東水珠正沿著他手背上突起的青筋往下爬。"第三回了,治癲"他突然開口,濟(jì)南煙灰簌簌落在水泥地上,癲癇第"閨女發(fā)病時把班主任嚇得不輕,醫(yī)院醫(yī)院現(xiàn)在全校都傳她身上有臟東西。山東"
這座淡黃色建筑總讓我想起老家泡發(fā)的治癲銀耳——門診樓像主菌蓋向四周膨出連廊,住院部則是濟(jì)南叢生的菌柄。候診區(qū)永遠(yuǎn)飄著消毒水與韭菜盒子的癲癇第混合氣味,輪椅碾過地磚的醫(yī)院醫(yī)院聲響和嬰兒啼哭此起彼伏。某個瞬間我突然意識到,山東這里或許是治癲全濟(jì)南最平等的場所:無論你是開寶馬的還是蹬三輪的,在神經(jīng)元的異常放電面前都得乖乖排隊(duì)。


走廊墻上"省級重點(diǎn)專科"的銅牌擦得锃亮,底下卻貼著張皺巴巴的尋人啟事。李主任的白大褂口袋里總揣著幾顆水果糖,查房時變魔術(shù)似的塞給哭鬧的小患者。"知道為什么兒童病房的窗簾是星空圖案嗎?"有次他指著正在做視頻腦電圖的男孩問我,"要讓他們覺得腦袋里閃的不是異常波,是銀河。"

藥房窗口前常演人間悲喜劇。上周見到個穿褪色工裝褲的男人,捏著處方單的手抖得像風(fēng)中的楊樹葉。收費(fèi)員報出金額時,他突然把臉埋進(jìn)臂彎里,肩膀聳動的幅度讓我想起女兒發(fā)病時的肌痙攣。后面排隊(duì)的大媽突然插話:"用我的醫(yī)保卡吧,反正額度用不完。"輕描淡寫得像是在菜市場讓人搭棵蔥。
康復(fù)科總充滿荒誕的詩意。我曾看見兩個少年在走廊練習(xí)平衡木動作,他們手腕上的住院腕帶隨風(fēng)飄動,像某種神秘的綬帶。王護(hù)士說有個女孩每次發(fā)作后都能背出圓周率后二十位,"比CT機(jī)還準(zhǔn)"。這讓我想起那些被閃電擊中后突然會彈鋼琴的案例——或許大腦本就是座隨時可能噴發(fā)的火山,醫(yī)學(xué)不過是在巖漿路徑上挖導(dǎo)流渠。
住院部天臺能看到千佛山的輪廓,病人家屬們常在這里交換偏方和電話號碼。老周說他試過把朱砂包縫在女兒枕頭皮里,隔壁床的碩士生立即翻開《臨床神經(jīng)病學(xué)》指出基底節(jié)區(qū)的位置。黃昏的光線里,科學(xué)和迷信在此奇妙地和解,就像樓下小販三輪車上并排擺著的電子血壓計(jì)和艾草香囊。
深夜值班室,實(shí)習(xí)醫(yī)生小陳的咖啡杯沿沾著唇膏印。"您說奇怪不,"她轉(zhuǎn)著筆帽,"課本上說癲癇是大腦異常放電,可我看那些家屬眼睛里的光,明明比EEG圖譜波動得更劇烈。"窗外急救車的藍(lán)光掃過墻面,將我們的影子短暫地釘在"醫(yī)者仁心"的書法作品上。
記得出院那天,老張閨女在門診大廳彈了首《獻(xiàn)給愛麗絲》。錯了好幾個音,但沒人打斷。李主任靠著導(dǎo)診臺輕輕打拍子,陽光穿過他胸牌上的鋼印,在地磚上投出小小的彩虹。或許真正的治療從來不在核磁共振室里,而在這些生銹的琴弦震顫的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