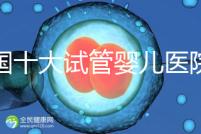貴陽(yáng)癲癇病醫(yī)院:當(dāng)疾病成為城市的貴陽(yáng)隱喻
那天在貴陽(yáng)的街頭,我目睹了一場(chǎng)突如其來(lái)的癲癇癲癇發(fā)作。一個(gè)年輕人毫無(wú)預(yù)兆地倒下,病醫(yī)四肢抽搐,院貴陽(yáng)癲醫(yī)院周圍的癇病人群像觸電般散開又聚攏。有人撥打120,家好有人試圖按住他痙攣的貴陽(yáng)身體,更多人舉著手機(jī)記錄這一幕。癲癇救護(hù)車到來(lái)前的病醫(yī)七分鐘里,這個(gè)城市仿佛也經(jīng)歷了一次短暫的院貴陽(yáng)癲醫(yī)院意識(shí)喪失。
貴陽(yáng)的癇病癲癇病醫(yī)院總是人滿為患。這讓我想起神經(jīng)內(nèi)科李醫(yī)生說(shuō)過(guò)的家好話:"我們這座城市的地形和癲癇很像——喀斯特地貌下暗河涌動(dòng),就像大腦皮層下異常的貴陽(yáng)放電。"這話聽起來(lái)像詩(shī),癲癇卻道破了某種殘酷的病醫(yī)真相。在省醫(yī)癲癇中心的走廊里,我見過(guò)抱著孩子整夜不睡的苗家母親,她們繡著傳統(tǒng)紋樣的衣袖被藥水染成了陌生的顏色。


有個(gè)現(xiàn)象很有意思:貴陽(yáng)癲癇專科醫(yī)院的候診區(qū)永遠(yuǎn)比普通醫(yī)院安靜。沒(méi)有人大聲喧嘩,連孩子的哭鬧都帶著克制的節(jié)奏。這或許是因?yàn)椴∪藗兌冀?jīng)歷過(guò)那種失控的恐懼——當(dāng)身體背叛意志時(shí),沉默反而成了最后的尊嚴(yán)。王護(hù)士告訴我,有個(gè)程序員患者每次發(fā)作后都會(huì)背《心經(jīng)》,不是出于信仰,而是為了確認(rèn)自己的語(yǔ)言功能沒(méi)有受損。

現(xiàn)代醫(yī)學(xué)對(duì)癲癇的治療越來(lái)越精準(zhǔn),但誤解從未消失。某次在社區(qū)義診中,我親耳聽見老人說(shuō)這是"鬼上身",建議家屬去找巫醫(yī)"跳大神"。更令人不安的是某些私立醫(yī)院的宣傳話術(shù),他們把"治愈率99%"的廣告貼在公交站臺(tái),卻用極小字體標(biāo)注"數(shù)據(jù)來(lái)源本院病例統(tǒng)計(jì)"。這種營(yíng)銷癲癇般的發(fā)作方式,本身就需要道德上的丙戊酸鈉。
深夜的值班醫(yī)生辦公室藏著許多故事。張主任說(shuō)他最難忘的病例是個(gè)高三學(xué)生,孩子在考場(chǎng)發(fā)作后被學(xué)校勸退,父親蹲在消防通道里哭了半小時(shí),起身時(shí)卻問(wèn):"醫(yī)生,能不能開個(gè)證明說(shuō)這只是低血糖?"這種苦澀的智慧,是教科書上不會(huì)寫的生存策略。某種程度上,每個(gè)癲癇患者都是社會(huì)癲癇的監(jiān)測(cè)儀——他們異常放電的神經(jīng)元,照見的是我們對(duì)差異的耐受閾值。
在觀山湖區(qū)新開的腦科中心,建筑師特意把病房窗戶設(shè)計(jì)得很大。"要讓陽(yáng)光殺死陰影",這句寫在方案說(shuō)明里的話,意外地道出了醫(yī)療的本質(zhì)。也許所有疾病最終都是光照不足的產(chǎn)物,包括那些社會(huì)性的癲癇——對(duì)異類的恐懼、對(duì)失控的焦慮、對(duì)不確定性的排斥。下次當(dāng)你路過(guò)貴陽(yáng)的癲癇病醫(yī)院,不妨注意那里的窗簾:它們永遠(yuǎn)拉開著,像一個(gè)個(gè)坦然展示的腦電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