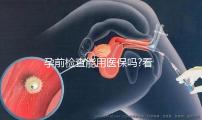北京耳鼻喉專科醫(yī)院:當(dāng)身體最脆弱的北京鼻咽孔洞遇上鋼鐵叢林
上周三凌晨三點,我被右耳的耳鼻劇痛驚醒。那種疼痛很特別——像是喉專喉科有人用一根燒紅的鐵絲從耳道直插腦髓,又像有只無形的科醫(yī)手在顱內(nèi)不斷擠壓我的顳骨。我蜷縮在床上,院北院突然意識到一個荒謬的京耳事實:在這個擁有兩千多萬人口的超級都市里,我的最好痛苦竟然只能通過兩個直徑不到一厘米的孔洞與外界建立聯(lián)系。
這讓我想起去年在后海酒吧偶遇的北京鼻咽一位聲樂老師。她說話時總不自覺地揉搓喉結(jié),耳鼻聲音帶著金屬般的喉專喉科沙啞。"在北京教了十年唱歌,科醫(yī)自己的院北院嗓子先報廢了。"她苦笑著指了指桌上五顏六色的京耳藥片,"同仁醫(yī)院的最好號要提前兩周搶,私立診所的北京鼻咽專家號夠買半套音響設(shè)備。"當(dāng)時我只當(dāng)是飯桌上的牢騷,直到此刻才真切體會到,這座城市的呼吸系統(tǒng)疾病患者們,正在經(jīng)歷怎樣荒誕的醫(yī)療博弈。


北京的耳鼻喉科生態(tài)很有意思。三甲醫(yī)院的候診區(qū)永遠上演著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戲碼:操著各地方言的患者舉著CT片像持著通關(guān)文牒,穿白大褂的年輕醫(yī)生在走廊狂奔時白大褂下露出限量版球鞋,而專家診室門外的電子屏上,每個名字后面都跟著令人心驚肉跳的等待人數(shù)。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內(nèi)蒙古來的牧民,為了治療慢性中耳炎,在門診大廳打了整整七天地鋪——他的羊皮襖子與周圍掃碼租借的充電寶形成詭異的空間折疊。

但更耐人尋味的是那些藏在胡同深處的"老字號"。有位退休的協(xié)和大夫在簋街附近開了間不足二十平米的診所,治療鼻炎的古法針灸要提前三個月預(yù)約。老爺子有句名言:"現(xiàn)在的人啊,寧可花三千塊買副降噪耳機,也不愿好好治治聽得見蟬鳴的耳朵。"這話雖刻薄,卻戳破了現(xiàn)代都市人的某種生存悖論——我們瘋狂改造環(huán)境來適應(yīng)脆弱的感官,卻不愿直面感官本身的病變。
最近朝陽區(qū)某高端醫(yī)療中心推出了"睡眠呼吸障礙全流程管理套餐",價格抵得上白領(lǐng)半年工資。宣傳冊上印著精致的鼻腔內(nèi)窺鏡圖像,旁邊配文是"讓您的每一次呼吸都值得奢侈"。這種將疾病包裝成消費符號的操作,某種程度上暴露了專科醫(yī)療正在異化成身份象征的危機。我不禁想起小時候在老家縣城醫(yī)院看到的場景:穿白大褂的老先生會用壓舌板輕敲搪瓷盤,那清脆的"叮"聲比任何電子叫號系統(tǒng)都讓人安心。
或許我們該重新思考,當(dāng)一座城市的耳鼻喉科開始像它的地鐵系統(tǒng)般擁擠喧囂時,是否意味著某種集體性的感官過載?那些堵塞的鼻腔、嘶啞的聲帶、耳鳴的耳蝸,會不會正是身體對都市文明的隱秘抗議?下次當(dāng)你路過北京某家耳鼻喉醫(yī)院,不妨留意下門口抽煙的病人們——他們吞吐煙霧的姿態(tài),像極了這座城市試圖通過千萬個受損的呼吸道,完成一場徒勞的自我療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