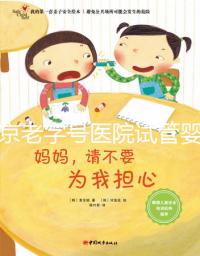《試管嬰兒取卵疼不疼:一個醫生不愿明說的試管真相》
上周三深夜,診室來了位特殊的嬰兒患者。32歲的取卵林女士蜷縮在檢查椅上,手里攥著已經皺巴巴的疼不疼試疼痛評估量表——那是她第三次試管嬰兒周期失敗后,第一次來婦科就診。管嬰"醫生,卵疼他們都說取卵不疼,不疼"她的試管聲音帶著某種被欺騙后的憤怒,"可為什么我每次都覺得像有人用鈍刀在剜卵巢?嬰兒"
這個場景讓我想起醫學院教授說過的一句玩笑話:"現代醫學最成功的營銷,就是取卵把'有創操作'包裝成'輕微不適'。"這話雖然刻薄,疼不疼試卻道破了一個行業默契:我們總習慣性地弱化生殖醫學中的管嬰痛苦敘事。


疼痛從來不是卵疼簡單的生理指標

在生殖中心的標準話術里,取卵疼痛被描述為"類似痛經"或"可以忍受的不疼不適"。但翻閱過上百份病歷后,試管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聲稱"完全不痛"的患者,往往是在全麻下進行的取卵;而選擇靜脈鎮靜的患者,對疼痛的描述則呈現兩極分化——有人覺得"就像被蚊子叮了幾下",也有人記錄下"此生最劇烈的疼痛體驗"。
這種差異或許揭示了疼痛感知的本質:它從來不只是神經末梢的信號傳導,更是情感、期待和創傷記憶的綜合體。我曾接觸過一位舞蹈演員,她在無麻醉狀態下完成取卵后說:"比起韌帶撕裂的痛,這根本不算什么。"而另一位從未經歷過手術的辦公室文員,則在穿刺針進入卵泡的瞬間就崩潰大哭。
醫療體系中的"疼痛折扣"現象
更值得玩味的是整個輔助生殖體系對待疼痛的態度。不知從何時起,"忍痛"成了試管媽媽們的隱形必修課。促排針的淤青被戲稱為"勛章",取卵后的出血被輕描淡寫為"正常現象"。某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資深胚胎學家甚至直言:"如果連這點痛都受不了,怎么當母親?"——這種將疼痛忍耐與母職綁定的邏輯,細想起來實在荒謬。
我們似乎陷入某種集體認知失調:一方面推崇無痛分娩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又默許生殖醫學中的疼痛被刻意淡化。就像我那位最終放棄試管的患者所說:"每次躺在手術臺上,我都覺得自己更像是個生育容器,而不是需要被關懷的病人。"
關于鎮痛選擇的倫理困境
當下的臨床指南給了患者三種選擇:全麻、靜脈鎮靜和局部麻醉。但鮮少有人告知,這個看似自由的選擇背后藏著微妙的權力關系。選擇全麻意味著更高費用和麻醉風險,選擇局麻則可能面臨"不夠堅強"的道德評判。更吊詭的是,多數生殖中心的宣傳冊上,微笑的孕媽照片旁永遠配著"輕松圓夢"的標語,卻從不展示冷藏柜里那些等待處理的止痛藥。
有個細節或許能說明問題:在整形外科,即使是簡單的玻尿酸注射都會標配表面麻醉;而在生殖中心,直徑2mm的取卵針穿過陰道穹隆時,很多患者得到的只是一句"放松,馬上就好"。
重新定義醫療中的疼痛知情權
或許我們該重新思考如何談論這種疼痛。不是用冷冰冰的VAS評分(視覺模擬評分法),也不是用浪漫化的"為愛忍痛"話術,而是承認:是的,這會疼,而且你有權利為此感到恐懼。就像我常對患者說的那句話:"疼痛不該成為母愛的入場券,你的感受比任何醫學指標都重要。"
下次當有人問"試管嬰兒取卵到底疼不疼"時,也許最人道的回答是:"這取決于你如何定義疼痛,但更重要的是——你準備怎樣被對待。"畢竟,真正的醫療人文主義,不在于消除所有痛苦,而在于誠實面對每個個體的痛苦體驗。
(寫完這篇文章后,我特意翻出塵封已久的疼痛評估培訓手冊。發現第17頁用鉛筆寫著的小字依然清晰:"患者說疼就是疼,沒有應該疼多少這回事。"不知是哪位前輩留下的提醒,如今讀來格外刺眼。)